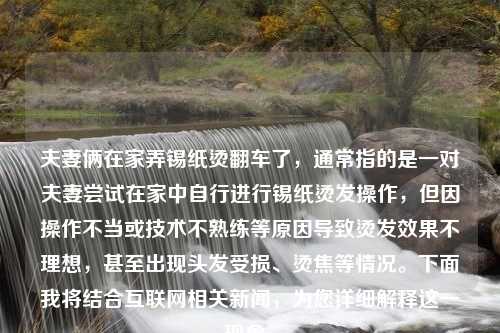如果美国重新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美元霸权将得以再度巩固,黄金牛市将终结。但这一次随着中国制造深入全球供应链,历史或较难重现。
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后,黄金价格整体承压,主要与其推崇的“美国优先”政策有关,推高了美元指数,导致黄金价格回落。从逻辑上而言,加征关税和驱逐移民将推高美国通胀水平,限制美联储降息空间,使得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利差保持高位;同时,加征关税、减税和放松管制等政策,旨在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增加消费者对美国国内产品的需求,总需求扩张意味着利率水平的抬升,二者将共同推升美元指数。美元指数的抬升意味着黄金价格面临阶段性压力。
但从中长期维度来看,观察这一轮黄金牛市的运行轨迹,黄金和美元已经呈现出“背离”特征,美元指数的走势对金价并不构成决定性影响。从历史走势来看,1971年至2015年期间,美元与黄金反向变动,二者相关系数为-0.52。但2016年至2024年期间,美元与黄金同向变动,二者相关系数为+0.45。从比价关系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之后共经历三轮美元周期,分别是1980~1995年,1995~2011年,2011年至今,这三轮美元周期中,美元指数的高点持续回落,而黄金价格中枢持续走高,黄金相对于美元的比价趋于上升。
对于黄金和美元的关系,从定价维度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投资视角,二者借助实际利率搭桥。美元指数是一个相对概念,由美国国债和欧元区公债的实际利差所决定。而黄金价格则是由实际利率决定,反映其机会成本;二是,货币视角,黄金和美元同为储备资产,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美元信用走弱的时候,黄金的货币属性发酵;三是,商品视角,由于黄金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所以美元指数的变化也会通过计价维度影响黄金价格。
当前美元和黄金的“背离”,背后隐含的是货币属性的发酵,即信用货币供应增加以及主权信用风险升高,导致黄金价值凸显。在全球经济多极化和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过程中,美元在货币体系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减弱,黄金正逐步脱离美元体系,成为不确定性时期的定价“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金崛起,正值美国霸权衰落。后续美国历届政府通过经济、社会、外交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最终对外赢得冷战,对内消除滞胀、实现生产力的提升,使美国经济重新焕发出巨大活力,黄金的魅影也暂时消退。“里根经济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美国经济成功摆脱滞胀困境,并通过放松监管和减税,促进了技术创新,为上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革命的诞生奠定坚实基础。
半个世纪后,历史的车轮再次转动。在美国对外债务扩张持续加深的背景下,美元信用的走弱,成为本轮黄金牛市的核心定价逻辑。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再度站到台前,想要通过促进制造业回流、平衡财政预算,维护美元霸权地位。
特朗普2.0时期能否终结黄金牛市,关键在于能否重塑美元信用,解决美国“双赤字”(经常项目赤字+财政赤字)的问题。而美元信用的前景取决于其国内改革的有效性。
从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主张来看,对外加征关税、对内减税、放松监管、削减财政支出等政策组合,与“里根经济学”的思想较为接近。我们参考里根时期的政策和经济表现,客观看待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效果。
1.贸易逆差能否解决?
里根时期缩减贸易逆差,主要是通过广场协议推动美元贬值,进而改善经常项目失衡的问题,但实际效果有限,汇率调整并未解决贸易失衡问题。1986年在广场协议的推动下,美元指数开始大幅走低,但1986~1987年间美国贸易逆差仍在持续扩大,1988~1991年才开始持续缩减,1992年之后尽管美元指数仍处在低位,但由于进口增长快于出口,贸易逆差再度走阔。
特朗普时期则主要通过发动贸易战的方式改善贸易逆差。2018年发动的中美贸易争端,中国通过转出口的方式予以应对,美国贸易逆差并未改善。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政策更加剧烈,试图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加征关税,解决这一问题,为美国创造“公平贸易”的土壤。
但实际上,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问题之一,是美国储蓄不足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上世纪70年代后,伴随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美元循环的建立,美国家庭储蓄率持续下降,2024年美国家庭净储蓄率不足4%,储蓄率不足必须通过贸易赤字大量利用外国储蓄才能平衡。同时,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必须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满足全球流动性。但由于美元扩张并无限制,这种持续的路径依赖,必然持续透支美元信用,形成反噬。
所以,依靠贸易争端和汇率调整解决巨额贸易逆差的问题并不现实,削减贸易逆差只是发动贸易战的由头,本质上是阻碍中国制造业升级路径,以抢占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先机。
2.财政赤字能否消除?
首先我们看里根时期的情况。
里根上台后,推出“大规模削减个人及公司所得税、大规模削减非国防开支、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放松政府管制和平衡预算”一系列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里根第一任期内财政赤字不减反增,第二任期内虽致力于削减财政赤字,但实际效果有限。
里根上台时,联邦债务总额为9143亿美元,里根任期中累计产生的债务达到10326亿美元,超过了1981年前历届总统产生的债务总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减税和增加军费开支。按照当时供给学派的观点,由于拉弗曲线的存在,减税会带来收入的显著增长,但实际情况并未发生,这是因为在紧缩通胀的时期,名义预算收入将会下降,在减税和紧缩通胀的时期,想要平衡预算,只能削减开支。但对内迫于政治压力,社会福利难以削减,对外为维护军事霸权,军费开支也难以削减,最终财政赤字的扩张不可避免。从实际情况看,1985年国防开支较1981年上升61.1%,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仅增长22.2%。
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出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高贸易逆差的现象,与当前情况类似。但是高汇率使得美国商品竞争力下降,出口锐减、进口猛增、贸易逆差持续走阔。当时据粗略估计,每出现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会减少2.4万个就业机会。按照1984年114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带来的失业人口高达300万人。同时,高赤字、高利率也引发西方国家资本外流和各国利率的普遍抬升。当时美国盟友认为,美国要领导世界经济走向复苏,首先要解决自己的赤字问题。1985年里根政府开始通过干预美元汇率、干预对外贸易、紧缩财政赤字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与里根时期不同的是,特朗普2.0时期想要通过加征关税以弥补减税带来的赤字上升。但从实际情况看,加征关税难以完全弥补财政收入缺口,反而可能抑制经济增长。
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测算,10%~60%的关税计划将在十年内筹集3.7万亿美元的总收入,20%~60%的关税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筹集4.5万亿美元的净新增收入。
根据现行法律基准,税务基金会估计,将《减税与就业法案》永久延长至2025年以后将导致10年内收入减少4.2万亿美元(动态基础上为3.5万亿美元)。
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的进一步减税措施,可能会使预算再增加4万亿美元。例如将公司税率从21%降至15%(十年内减少约2000亿美元),免除小费收入税(-3000亿美元),终止对社会保障福利征税(-1.3万亿美元),免除加班收入税(-2万亿美元),结束对外国收入征收美国所得税(-1000亿美元),汽车贷款利息税收减免(-1000亿美元)。
与里根时期类似的是,这一次美国财政支出削减的空间依然有限。
2024财年,美国联邦支出约6.75万亿美元,赤字为1.83万亿美元。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坚称不会削减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这些项目以及公共债务的利息支付占联邦支出的61%,共计4.09万亿美元。
在剩下的2.66万亿美元中,有两项支出难以削减,分别是:1)医疗补助计划,2024财年支出为6200亿美元,牵涉7000万名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险,削减难度较大;2)退伍军人管理局,2024财年支出为3200亿美元。这笔钱用于资助退伍军人医院,用于治疗在战斗中受伤的士兵,同样不太可能削减。
因此在剩余的1.7万亿美元预算项目中,可能的削减项目包括终止清洁能源政策支持、减少浪费性支出、关闭联邦教育部等,联邦预算委员会测算,预计十年内将节约1万亿美元。这距离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提出的2万亿美元联邦预算削减目标仍有相当的差距。
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利率上升等因素将使得强制性支出和利息支出的需求不断增加。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预计2034年社会保障福利支出约为2.48万亿美元,较2024年增加近1万亿美元;2034年医疗保险支出约为1.74万亿美元,较2024年增加约8000亿美元;2034年公共债务净利息支出为1.7万亿美元,较2024年增加约8000亿美元。即未来十年内,刚性财政支出共计增加2.68万亿美元。
因此,特朗普2.0政策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财政赤字的扩大,但对于削减财政赤字、实现预算平衡而言,仍然存在重重阻力。严格的财政支出削减对于中期选举、国内政局稳定、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都提出了较大的挑战。
走出财政困境的更可行方式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财政收入增长,从而化解债务危机。否则,美国大概率将延续债务货币化路径。
1993~2000年,伴随信息革命的到来,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和财政收入增长,使得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得以化解。当前正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AI浪潮的到来有效提升生产率,未来随着应用层面的持续扩大,有望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生产力的跃升将消除美国滞胀隐患。未来如果美国重新主导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美元霸权将得以再度巩固,黄金牛市将终结。但这一次随着中国制造深入全球供应链,历史或较难重现。未来中美在产业领域的博弈,将极大决定美元、黄金的长期走势。
(高瑞东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标签: